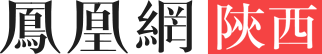传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护照——张贤亮先生十年祭


独家抢先看
文/高建群
一
一些年前,我们的朋友、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先生获得某奖后,一位美国女访问学者来西安。在西北大学座谈时,她问我,高行健获某奖,他们早就预料到了,一定会受到中国体制内的抵制,但是,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,来自体制外的抵制似乎更强烈一些。
二
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。我说,长篇小说《灵山》的水平,我在中国可以为你找五十个这样的作家。记得我掰起指头,谈到的第一个中国作家,就是张贤亮。我说,张贤亮在《绿化树》中,在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中,在《习惯死亡》中,他对苦难的理解和诠释,他对中国风格中国传统的继承,都是《灵山》所没有能够达到的。
三
《绿化树》中马缨花蒸馒头时,指头旦儿给蒸熟的馒头上留下的几个簸箕几个斗,那是神来之笔呀,细节描写中的千钧之力呀!而在《习惯死亡》中,在劳改农场,吃饭的时候,一群挖战壕的目光猥琐的犯人,围着战备壕中一具挖掘出来的女骨,流着涎水,把她想象成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只所以将这一堆白骨判定为女骨,是因为这女骨上的飘飘长发还在,还没有腐烂。
四
《习惯死亡》原名叫《无桅之帆》。这部长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,真是遗憾。张贤亮夫人,尊敬的冯剑华女士说,《习惯死亡》是张贤亮写得最艰难、最认真的一本书,整整一个冬天,他都盘腿坐在烧热的炕上,就着一张小炕桌,吭哧吭哧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抠。
五
记得西北大学那个小型的座谈会,在座的还有供职于北大,后被打成右派,流落到西北大学任教的张华老先生,还有年轻的学者、西大教授杨乐生。席间,我曾请教张华老,我说,您是吴宓先生的入室弟子,你能用一句话,总结出吴宓对中国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。张华老回答说,吴宓发现了一条历史铁律,屡试不爽,这条铁律就是,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,不是走在最前边的人代表着真理,也不是走在最后边的人代表着真理,而是走在中间的那一群灰色大众。尽管这个发现很无奈,但是这是真的。我这是插言。
六
我最后一次见到贤亮老师,是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十月二十五号。我去额济纳看胡杨林。胡杨林的全盛时间是每年十月的二十三号,那一刻,好像得到大自然的某项指令似得,在秋日的炫目的阳光下,所有的胡杨树叶会在这天中午,突然变得金碧辉煌。看完胡杨林,又在大蒙古包住了一夜,第二天返回银川,然后我通知宁夏文联,过江东、拜乔老,我要去拜访贤亮老师。
七
那时我还不知道贤亮老师已经查出有病。早上驱车来到影视城门口。大门下面挖了个深深的壕沟,上面一左一右两扇吊桥。两个兵丁,分列左右。一个拿着杆长矛,背上圆心中,写了个“兵”字。一个拿着把鬼头刀,背上圆心中,写了个“卒”字。我站在城外,扬声喊道:禀报你们张主席,就说陕西高主席来了。他说过,这影视城,高主席当一半的家!见我这样说,一个兵丁站立不动,将鬼头刀背在身后,另一个扛着长矛,一阵小跑,回去报讯去了。一会儿工夫,身穿藏青色套装,系着飘带的马总出来了,她扬扬手,示意把吊桥吱吱呀呀地放下来,然后我们的车就进去了。

八
张贤亮先生抱着一个小毛孩,在一个小院子里踱着方步等我。他永远像个大人物那样衣冠周正,腰板笔直。马总悄声在我耳边说,贤亮身体欠佳,你不要叫他激动,谈话最多半个小时,就让他休息。于是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室,喝茶。那天都说了些什么,我都不记得了。只记得他反复说过“当代文坛是绕不开我张贤亮的”这句话。后来得知他患了不治之症的消息后,我才知道他当时的心境以及说这句话的深意。
他还说了一件事。他说,有一年北京开作代会,会后是主席团会。他是主席团委员。会后,出了门后,一个人上来套近乎,抱了一下他的肩膀说,祝贺某主席连选连任。他反应式的一回头,这人才发现认错人了。那人很尴尬,他也很尴尬。那一阵子流行拷花呢黑色半大衣,与会者有好几个人穿着。
贤亮先生好几次给我说过这事。这一次又说,可见他也不能免俗,很在意这个虚职的。

九
随我一起去的宁夏电力的老总,拿出个红包,说他们那办了个创作会,希望张主席去见见大家,讲个课。张贤亮头一摆,高傲地说,我去年影视城的税收是一百五十万,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
那次他还将自己新出的一部长篇送给我,书名好像叫《一亿六》。这本书我回来翻了翻,但是始终不明白这“一亿六”是什么意思。那天他费力地解释了半天,我也没听明白。是说有一亿六个精子赛跑,去接触那个卵子,最后有一个精子胜出,一个天选之人诞生了。这个人就是作家张贤亮。是这样吗,我不知道。
最后与他告别时,他拿出事先写好的一幅书法作品给我:“大漠落日自辉煌。建群老弟晒正”。字已经装进了袋子里了。贤亮又从袋子里取出,捧着字为我介绍了半天。我说,上一次在影视城,咱俩进行书法比赛,你为我写的是“春秋多佳日,西北有高楼”。而我为你写的是“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”。
整个会面期间,空气中有一种哀恸的感觉。直到我告别走远,贤亮老师还站在会客室的门口,像在望我,又像在望着空旷的天空。
十
贤亮先生站在那里,怀里继续抱着孩子。他把孩子举起来,骑在自己的脖子上。而这个被称为马总,或者被称为马缨花,或者被称为马红英的牧民的女儿、大河套的女儿,轻轻地用手扶着他的肘。

十一
贤亮先生去世的第三年,北京开文代会,我专门找到张夫人剑华嫂子。我说我给你谈两件事。一是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发了篇悼念贤亮先生的文章,名字叫《大漠落日自辉煌》,你们将来出纪念文集时,将它收上。二是马总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,我一直放心不下这事。我的意思是让她继续担任影视城总经理,权当是给她一个饭碗吧!这样贤亮先生九泉之下也会安息。剑华说,你说迟了,马总已经离开影视城了。我问她到哪里去了。剑华说,她到银川城一家文物商店上班去了。我说,不可改变吗?她说,不可改变!我在那一瞬间眼泪突然涌出来了。我说:“嫂子,那就当这话我没有说!”
十二
镇北台影视城我许多次的去过。陕西和宁夏离得很近。记得第一次贤亮先生陪我去看影视城,这里还是一个十分荒凉的所在。贤亮先生说,从劳改农场去银川市,要路经这里。当初这里叫镇南堡,堡子里还住些牧民。通常,他要在这里歇息一下,住上一晚上。
后来他将这里开发成影视城。宁夏有什么呢,宁夏有“荒凉”,所以我这主打的就是一个“出卖荒凉”。将这里打造出一个旅游景区,游客们从这里带走的是两脚泥土,留下的是他们口袋里的钱。
我说张老师你咋这么有经济头脑呀,我们陕西作家就没有你这化学脑子。贤亮先生说,你们陕西作家一群农民,把自己名字改了,以为自己这就不是农民了,我告诉你,骨子里的东西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。
他还说,我家三代都是资本家。我坐牢时就知道改革开放的大潮有一天会到来。于是就开始学习《资本论》。
他还说,全国政协开会,把我分到文史组咧,我很不高兴。我对他们说,下一次,我就该去参加经济组了。

记得那一次,他给办公室桌子的玻璃板上,铺了些报纸,报纸上面放了宣纸,要我写上“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”字样。后来制作出的那横放的招牌,是不是我写的这字,我不知道。或许那字是贤亮先生自己操刀写的吧。
十三
贤亮先生说,镇北堡住的这些牧民,怎么驱赶也驱赶不走。牧民们说,当年马步芳马主席,手提两把盒子枪,想把我们赶走,也没有做到。你个张主席,一个手无寸铁的白面书生,想把我们赶走,你就把脚蜷了吧!
他说,最叫人不能接受的事,电影《红高粱》刚拍到“九九青杀口”那一场,牧民们赶着羊群,像云彩一样,从堡子那个月亮门漫山遍野地过来了,叫人哭笑不得。
他说,后来他想了个办法,将这些牧民的孩子招为员工,又为他们制作了工作服,然后拉到广州,培训了三个月。孩子们回来后给家长做工作,就这样镇北堡居住的牧民,陆续搬走了。
十四
那次,马总领我参观影视城,那时影视城已经初具规模。马总拿着个大喇叭,说着银川普通话。他来到那个横放着的牌子面前,两只眼睛放着光,望着天空,朗声说道:敬爱的张主席教导我们,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!又来到堡子中间那烧酒坊里,把双脚往地上墩了墩,说这地下埋的张艺谋导演的一双破球鞋。拍完《红高粱》,张导将鞋埋在这里,以作纪念。最后,又来到城的一角那个月亮门上面,说原来的门坍塌了,这是为拍电影,重新造的。
十五
记得有一次我和宁夏的作家们吃饭时,我对他们说,请你们理解张贤亮,包容张贤亮,欣赏张贤亮,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,都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,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别人。你们和张贤亮先生共同生活在银川的这一片天空下,是你们的幸运,因为大师就在身边,他的成功将激励你们。而同时,也是一种不幸,因为这棵大树占了太多的阳光,从而遮蔽了你们——大树底下不长草呀!
十六
贤亮先生五七年因《大风歌》而被打成右派,承受不公正对待,有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。那一年在深圳开会,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的作者,丛维熙老先生说,大家都说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父,丛维熙是大墙文学之叔,我认可这说法。
还有一次,2014年度中国图书节在贵州召开,贵州文联主席欧阳黔生先生请我吃饭,老作家何士光作陪。席间说到张贤亮老师的病,士光老师说,我想和他通个话。于是我拨通了贤亮老师的电话,可是那边已经没有人接了。
张贤亮老师的复出,宁夏作家李唯说,是他在《朔方》当编辑时,发现的自由来稿。《宁夏日报》的副刊编辑秦川牛说,是他从一大堆自由来稿中,发现的。而坊间的说法,大多认为是光彩照人的冯剑华编辑发现的,并且将这位才华横溢的奇才揽入怀中,最后成为她的丈夫。
这些传闻我们都认可,人们总是怀着对文学的一种敬畏感,来说这个话题,希望自己和那些非凡的人,命运有过交叉。
十七
有一次,宁夏电视台台长徐赛给我打电话,约我去银川,谈我的中篇《雕像》改编电视剧事宜。于是我偕号称长安第一风流才子的老作家张敏,青年文化学者石岗,坐了班车去银川。徐台说,《贺兰雪》刚拍完,这是导演陈家林住的房间,他前脚刚走,你就住这儿吧!
那天我们去拜会张贤亮。贤亮先生说要和我比书法。我们去的好像是另一个地方,房间很宽敞,一个很大的老板桌,贤亮先生翘着二郎腿,坐在一个转椅上,身后,一个年轻的秘书小姐给他捏着肩膀,捶着背。我见状说,文化人熬到这份上,这叫成了精了。我问,这老板桌是文联给你配的吧!贤亮先生说,不是!文联给配的那白木桌子,我早让收破烂的收走了,这老板桌,是公司给本董事长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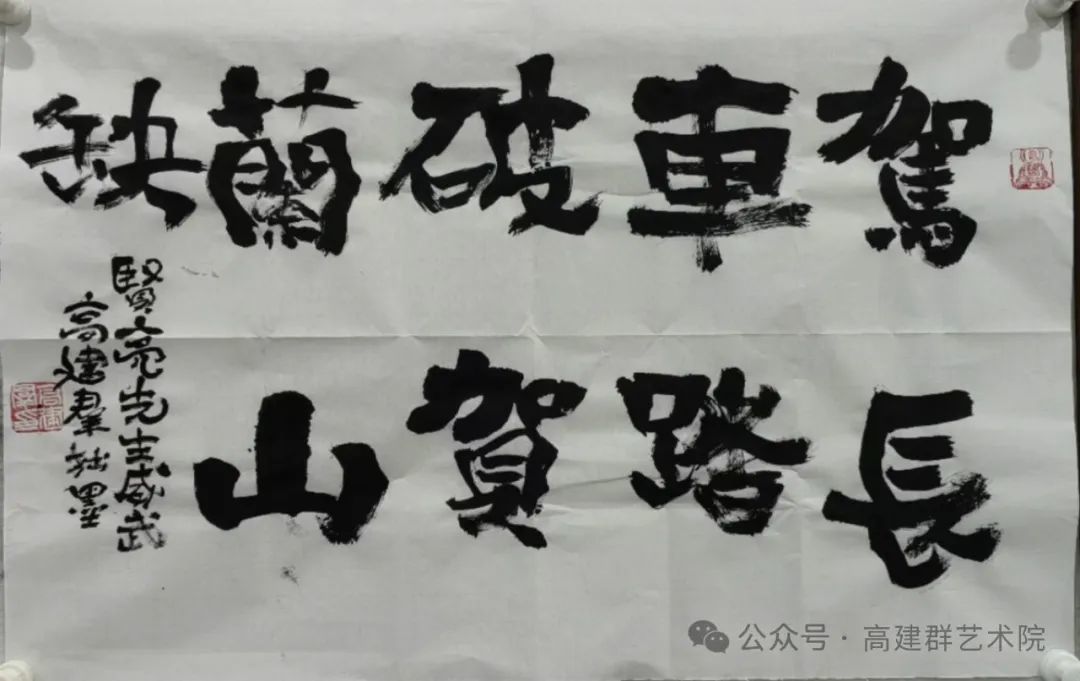
那天以文会友,写字,前面说了,我给贤亮写了“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”字幅,贤亮先生则给我写了“春秋多佳日,西北有高楼”字幅。
西影厂文学部张敏,和贤亮十分熟。当年吴天明厂长想将贤亮先生的《浪漫的黑炮》改成电影,派张敏来说。张敏的性格和贤亮有些相似,都好做大言,都有一些自大狂。那次两人一谈,说到热火处,贤亮先生便授权了,区区两万块钱,买走了改编权。这把吴厂长给高兴坏了。后来电影拍出,叫《黒砲事件》,黄建新导演,该片后来成为西部电影代表作之一。后来黄导提出,还想拍个续集。这剧本是张敏先生亲自执笔,电影名字叫《错位》,也是西部电影的代表作之一。
十八
张敏要贤亮先生为他写八个字:“以笔作剑,横扫文坛”。贤亮在大家的夸赞下,将字写出。张敏在傍边拍手叫道:赶快签上你的名字。明天,我就把这字印在背心上,然后全国各地到处跑,就说,张大师说,我张敏气壮如牛,以笔作剑,横扫文坛!
贤亮先生是个何等聪明乖巧的人,他皱皱眉头,也觉得这样写不妥。可是字已经落到纸上了,也不好收回。只见他,背着手在房间转了一圈,回来后提笔落款:录张敏老弟豪言。张贤亮。
皮球就这样又踢回张敏脚下了。张敏提起字,搂着张贤亮肩膀说,你狡猾!

十九
还有一次重要的银川之行。央视十频道开播前,要拍一个开场大戏,专题片名字叫《中国大西北》。央视才子童宁担任总导演,新疆作家周涛,北京作家毕淑敏,陕西作家我,担任总撰稿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有过军旅经历,对大西北如数家珍。另外,新疆经济报副总编辑朱又可,担任编辑、摄影和助理。
毕淑敏大姐对我说:“老高呀,咱们俩这名字呀,都不浪漫,缺乏想象力。你的名字,像个乡镇干部的名字,我的名字,像个居委会大妈的名字!”我说,同意同意,严重同意。
那次自治区书记毛如柏会见了我们。而后来吃饭,按照朱又可的回忆,是贤亮先生在影视城请的。席间请了银川市委书记刘忠一起用餐。
记得饭局上,贤亮先生喋喋不休地,向领导诉苦。说的是银川街道的钟楼上,安的那个视频广告的事。城管部门要他拆掉,说不伦不类,有碍市容观瞻。贤亮说,领导呀,钟楼建筑是传统,视频广告是时尚,二者相互辉映,增加了咱们银川市的文化多样性呀!
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,叫我印象深刻。刘忠书记手一挥,好像要讲话的样子。结果把桌子上的一瓶宁夏干红带翻了。酒瓶倒了,流了一桌。刘忠有些尴尬。谁知贤亮一下子站起来,两手一拱,一叠声地说道:好事来了,恭喜书记,你要大发了。
书记有些不解。贤亮说,酒泼了,这个“泼”字,一边是三滴水,一边是发字。三滴水就是酒呀,发就是代表你要大发呀!
好话最是受听,刘忠听了很高兴。然后贤亮先生把嘴巴搭到我耳边,小声说:“老弟,你要跟我学着点,这叫给领导点眼药水!”
二十
吃完饭的第二天,徐台打来电话说,张贤亮请客,没有叫冯剑华,冯主席红颜大怒。冯主席今天中午要请你们吃饭,而且点名不让张贤亮参加。
那顿饭十分丰盛,是在一个叫“羊肉庄”的地方。全是羊肉的各种做法。银川人好像都知道这地方。
冯老师我也认识很久了。1983年陕西作协组织了个黄土地诗会,我们曾去银川,拜访过《朔方》编辑部。记忆中的冯剑华,乌亮的头发,剪成个刷刷头(齐耳短发),高挑的个子,一身藏青色的套装,轻便皮鞋。我想,当年的劳改释放犯张贤亮,一踏进《朔方》编辑部改稿,一定是一脸惊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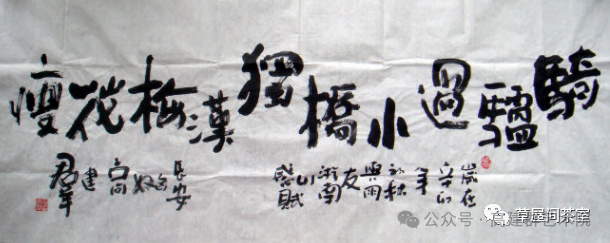
那天我给冯主席写了个字幅,叫“骑驴过小桥,独叹梅花瘦”。我是感慨生活把这样一个心高气傲的女人,这个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,已经折磨得如此憔悴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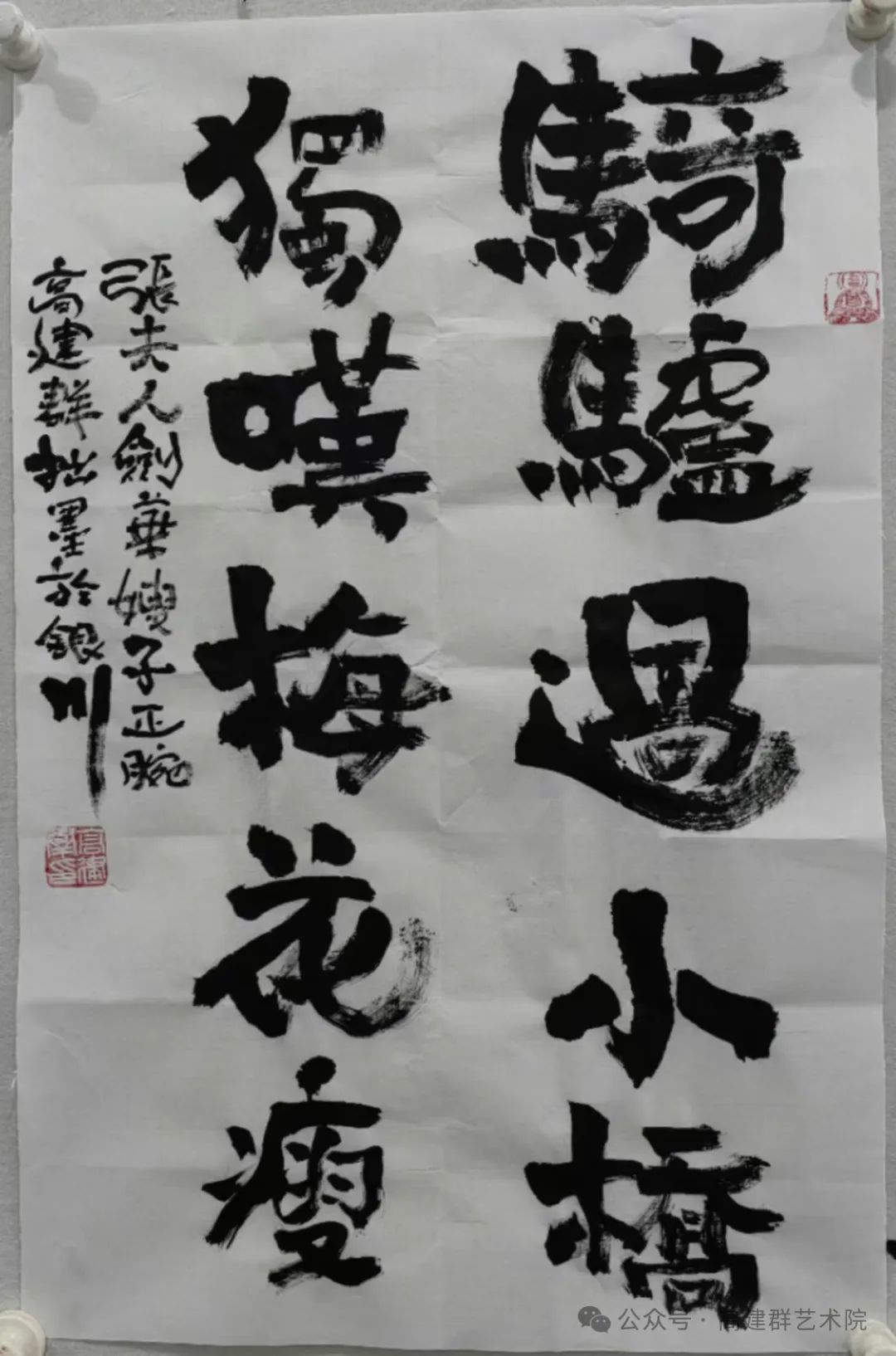
二十一
我第一次见到张贤亮先生,是在1991年7月下旬。是时,中国作协在西安颁发第四届庄重文文学奖。张先生是评委,我是获奖者。
中国作协是张锲书记来主持,这次获奖者侧重大西北,所以放在西安来颁。宁夏的获奖者之一叫李唯,一个留着长发,穿一件黑T恤衬衫的帅哥。庄重文老先生是香港企业家,他没有来,打发他的儿子,提了二十万人民币,来给大家颁奖。
贤亮先生来得迟了点,已经晚上八点了吧。他是去贵州讲课,坐飞机从贵阳赶过来。他带着一个英俊的小男孩。他说孩子八岁了,正好放暑假,带着他出来。
大会让我陪他。“是《遥远的白房子》的作者吗?”他很热情。他说咱不吃灶上那饭了,咱上街去吃,会上给我发了一千块的评审费,这叫无功受禄,咱们上街,把它消费了吧!
西安人民大厦出门向东,叫东新街,西安市政府把那里搞成个饮食一条街。一长溜的小推车,上面挑着红灯笼。陕西作协的李秀娥在前面带路,我们一家一家吃过去。
记得,贤亮先生指着街上电影海报上那个“靓男俊女”的“靓”字,问我那怎么念。我摇摇头说,我也不知道。
那天大约他还处在贵州讲课的激情和思考中,我们一路走一路吃,期间,他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观点。这个观点后来一直像烛光一样照耀着我的创作。
他说,要为一个民族写出它的史诗,有个窍门,那就是寻找它的断代,将它的断代史写出来了,这个民族的史诗就写出来了。
他说,贵州那么穷,地无三尺平,人无隔宿粮,但是,苗族妇女,她们人人都有一幅十几斤重的银首饰,平日锁在箱子里,遇到节日时戴到头上。
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这个民族的历史上,曾经是一个生活在温柔富贵之乡的民族,后来因为某种原因,发生了一场变故,他们举家举族从平原地搬到这十万大山之中。那银首饰保留着他们那遥远的民族记忆。
贤亮先生反复说,将这一段绝代史写出来了,这个民族史诗就写出来了。我在贵州的讲课中反复讲这个,不知道贵州的朋友们听懂了没有?!
二十二
在尊敬的贤亮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,我写下上面这些沉重的文字。写的时候我老眼昏花,眼前始终闪现着先生的那音容笑容。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。时代使然,那个时代涌现出许多特立独行的人物,张贤亮先生是那个文学时代的一面旗帜。
这篇十周年祭,他们说早就给我约了。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忙我的一部长篇小说《中亚往事》的事,闭目塞听,精神恍惚。直到三天前,加了《朔方》主编火会亮先生的微信后。他告诉我,冯剑华老师一再说,一定要我写篇悼念文章,说我最了解贤亮。冯老师这话,分量很重。所以我推开一切杂务,用了三天,完成这篇文字。
贤亮先生是个带着一路传奇,走完一生的人。英国小说家毛姆说,传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护照。“当代文学史绕不开我张贤亮的!”此一刻我又记起他那略带几分悲壮色彩的话。
我稍稍觉得,这句话除了气壮如牛之外,还隐约露出一丝对于被时间可能遗忘的担忧。
2024.7.31——8.2于西安
本文选自《朔方》2024年第9期
供稿单位:高建群艺术院